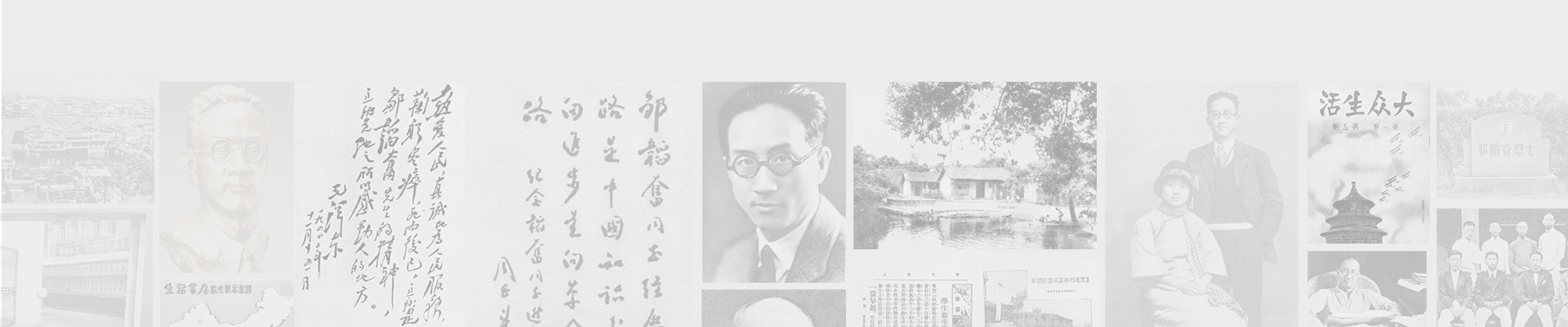邹韬奋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从邹韬奋与胡适的分道扬镳谈起
发布时间:
2025-11-24 14:00
作者:
韩庆祥 肖伟光
来源: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韬奋精神的丰富内涵与当代价值(笔谈)》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新时代我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面对近代以来的社会剧变,中华民族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在艰辛守护和不懈探索中赓续中华文脉,巩固文化主体性。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文化抗战一面旗帜的邹韬奋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邹韬奋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主要体现在其对革命文化的丰富上、对大众文化的传播上。我们可以从邹韬奋与胡适的分道扬镳来谈起。
胡适是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但不少与其共过事、甚至崇敬过他的人,最后都选择了与他不同的道路。这其中,南陈北李和邹韬奋的选择最有代表性,前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后者则被中共中央追认为中共党员。如果说胡适与南陈北李分道扬镳是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自然分流,那么,邹韬奋与胡适的分道扬镳则是抗战期间国统区文化界的自然分流。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界,胡适与邹韬奋是两颗耀眼的星辰——前者以北大为舞台,以理性启蒙的姿态推动社会改良,在新文化运动中骤得大名;后者以《生活》周刊为阵地,坚持“永远立于大众立场”和“竭诚为读者服务”,身体力行倡导“言论要完全作人民的喉舌,新闻要完全作人民的耳目”“笔柄千秋唤救亡”,是抗战期间文化领域的领军人物。两人早年曾因共同的“改良”底色产生交集,邹韬奋更一度将胡适视为思想引路人。彼时的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问题与主义”论战中自由主义的代表,其倡导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务实态度,以及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坚守,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深远。邹韬奋早年在南洋公学、圣约翰大学学习,后任职于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生活》周刊的初衷便是“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邹韬奋接手《生活》周刊后,先后发表过五篇胡适的文章,还发表了二十多篇介绍评述胡适言论的文章。但邹韬奋后来清醒地认识到:“‘修养’不应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却要注意到社会性……是要以集团一分子的立场,共同努力来创造新的社会。”这一转变是邹韬奋在办刊办报实践中、在与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深刻互动中逐渐发生的,标志着邹韬奋本人对于大众文化的认知觉醒,是后来他高高举起文化抗战大旗、高扬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与基础。
具体来说,邹韬奋自接手《生活》周刊后,进行了三次重要的导向性调整。第一次将其从内部机关刊物转变为面向广大青年讨论个人修养的趣闻杂谈,第二次转变为应着时代的要求关注社会问题,第三次转变为揭露黑暗现实、宣传爱国主义、倡导抗日救亡的舆论主阵地,成为在青年中有较大传播力的时事刊物。事实上,《生活》周刊从每期发行量只有两千八百份(其中多数还是赠阅),到发行量破万、破十万,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邹韬奋迅速调整办刊方向,公开宣告“与国人共赴国难”,将《生活》周刊转变为以“团结抗敌御侮”为目标的“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销量增至15.5万份,创造了当时全国杂志发行量纪录,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在《生活》周刊办刊理念的转变过程中,邹韬奋与胡适也就渐行渐远。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胡适明确表示,“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会导致社会的轻视和厌恶”,并且劝学生要“安心向学”。邹韬奋撰文批驳道:“有些人一再发挥知识的重要,力劝学生‘埋头’到课堂去。我们以为求知识不在读死书,不在‘洋八股’,更不在养成‘顺民’式的教育;在民族这样危险万状的时候,知识须和民族的解放斗争联系起来,在实际行动和实践中才有真知识可以求得。”这次还是用“有些人”来指代的不点名驳斥。1936年,邹韬奋在《送胡适博士赴美》一文中明确指出:“胡适博士最近的政治主张,有许多地方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而且胡适博士一面主张把东北四省送给外人,一面又主张中央下令讨伐西南,薄于己而厚于人,也未免过火了些”,指名道姓、毫不掩饰。邹韬奋与胡适的分野,本质上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语境下,对道路选择与角色定位的不同回答。胡适始终将自己定位为社会的观察者与理性的建言者,他相信知识分子的使命是通过知识传播与制度设计,引导社会平稳过渡到现代文明。这种立场在和平时期或许具有进步性,但在民族危机空前严峻、底层民众苦难深重的时代,其渐进性与精英性难免显得脱离实际。邹韬奋则选择了行动者的道路。他从办刊、办书店到组织救亡运动,始终与普通民众站在一起,将民众觉醒视为社会变革的前提。他对胡适的疏离,不仅是对具体观点的否定,更是对“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改良”的超越——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结合,通过动员最广泛的民众力量,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
胡适当时早已经是学界名人、文化名流,邹韬奋作为一个年轻的出版人,与这样一位大人物直接对立,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而作为一位敢于为真理而斗争的爱国者,正是在与当时的文化名流的思想交锋中,邹韬奋完成了思想的蜕变与升华,完成了先进文化、大众文化的传播,在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事业上刻下了自己的独特印记。
在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迸发出强烈的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意识体现为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强烈民族自尊、体现为强烈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所指出的:“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在这个过程中,邹韬奋对于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最大成绩,就是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大众一边、站在历史进步一边,通过办报、出版等方式,积极传播抗战文化、大众文化,揭露黑暗、弘扬正气,将文化传播作为民族战斗的武器、将大众传播作为唤醒同胞的利器,为“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就宣传教育的作用来说,韬奋对于同时代的影响,却比鲁迅还要来的普遍”,胡愈之的这个观察是很深刻的,看到了邹韬奋在“宣传教育”方面的独特优势与作用。邹韬奋所创办的《生活》周刊发行量达15.5万份,《大众生活》达20万份,《全民抗战》达30万份,生活书店遍布全国14省55城、成为当时最受青年人喜爱的出版机构之一,这些实打实的数字充分证明了邹韬奋是那个年代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所信任的媒体人、文化传播者。邹韬奋在《坦白集》的弁言中坦言:“在这集子里,关于团结御侮的文字最多,这是因为这个问题是中国当前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自忘其无似,尽我的一知半解,参加研究,以供国人参考。我所觉得欣幸的是这个问题现在已引起了全国人的严重注意和讨论。”这个无不骄傲的告白,袒露了邹韬奋心底最在意的永远是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邹韬奋在苏联考察颇受触动,加上在英国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从心底已经认同了马克思主义,认同了中国共产党。这种认同,在邹韬奋文字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充分发掘人民群众的力量。“大众的伟大的力量”是邹韬奋笔下反复强调的一个关键词。“我们在这样艰危的时代,应该培养大众的伟大的力量”,因为“大众的伟大的力量”是这个时代“最最重要的象征”。在民族危亡之际,实现民族解放所能依靠的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不能指望少数自以为是的所谓精英或者虚无缥缈的外部势力,这是邹韬奋在实践中得出来的结论。1935年11月16日,海外流亡归来的邹韬奋创办了《大众生活》,明确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这三大目标——在汪洋大海怒涛骇浪中的我们的灯塔——是当前全中国大众所要努力的重大使命;我们愿竭诚尽力,排除万难,从文化方面推动这个大运动的前进!”1936年6月7日,邹韬奋在《生活日报》创刊词中明确揭示:“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这也是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 “从文化方面推动这个大运动”或者说“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这就是邹韬奋的时代使命,他极为出色地完成了这个时代使命。正如端木蕻良所说的:“韬奋先生和他所开创的《生活》为什么在全国人民心中有着这么广泛的吸引力,就是因为他代表了人民的力量,说出了人民要说的话,成了人民要求抗战的代言人,因为他生活在人民中间,人民便支持他。”
不仅是报刊。生活书店传播网络的构建,也是整个革命事业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样为抗战文化的大众化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一革命文化的堡垒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进步读物的出版发行中心,并在抗战期间出版了大量的进步刊物和书籍,对于传播进步思想和抗日主张,冲破反革命文化“围剿”,为进步文化工作者开辟战斗阵地,引导广大青年提高思想政治觉悟,走上革命道路,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有关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国内共出版‘红色读物’四百余种,而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就出了二百种左右,其余为解放区的出版社所出。”三联书店在出版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1949年7月,中共中央在《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明确:“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领导下的书店”“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等,做了宝贵的工作”。这是党中央对三联书店、对邹韬奋的高度认可。198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再次发文,指出:“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及其联合后的三联书店,在建国前实际上起到了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出版发行机关的作用。其性质与新华书店一样,其工作是在我党领导下进行的,其经营目的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我党的方针政策,在扩大革命影响、唤起广大青年投身革命、冲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化围剿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关于确定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进步团体及三联书店成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通知》,中共中央组织部组通字〈83〉34号)。三联书店与解放区的出版机构密切配合,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
与我们党领导的游击队相呼应,邹韬奋称自己从事的工作是“文化游击队”。邹韬奋还把生活书店员工比喻为“为文化事业冲锋陷阵的一个小小军队”,把自己办的报刊比喻为“喇叭手”“高喊当前民族应走的道路,怎样走法”。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大量报道并深刻分析与抗战有关的国内国际形势,“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敢于为人民主持正义,敢于为真理而斗争,真正做到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抗战》三日刊全面反映人民大众在抗战时期的迫切要求,一度成为抗战时期旗帜性刊物,被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赞誉为“今日抗战中之指针”。“在这抗战的时期,笔杆应该和枪杆联系起来,文化食粮的供应应该和军火的供应配合起来”,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民族解放、一切为了人民利益,这就是积极推广大众文化的现实指向,这就是邹韬奋的文化自觉。
邹韬奋和他的合作伙伴,不仅成功构建起了大众文化的传播体系,为提振抗日士气鼓与呼,而且,还躬身入局,参与创立并推动了救国会运动的开展。1935年年末,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在上海发起成立救国会,致力于全国团结一致共同御侮的局面形成,次年11月遭到南京政府的拘捕、关押,史称“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事件”激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得到包括中国共产党以及宋庆龄、爱因斯坦、杜威、罗素等国内外名流在内的声援与营救,为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这些史实是大家所熟知的。但是邹韬奋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很多人或许并不熟悉。举例来说。《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呼吁“负有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立即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而领导救国运动”,“我们现在要先组织自己,用集团的力量,来负担我们时代的任务”,这类重要历史文献,邹韬奋都是重要参与者、领导者。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第二次宣言》中,救国会明确提出“反对文化统制,反对文化界汉奸”,旗帜鲜明地抵制文化奴性,争夺独立自主的文化话语权,要求文化自主权。当时,国民党政府压制新闻出版事业,采取封禁、取缔等手段对一切不利于自身的舆论进行打压,破坏了言论生态,扭曲了新闻媒体的价值作用。因此,救国会要求“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确保将国家民族遭遇的实际情形向读者、民众传播,以免当局政府混淆视听,欺骗民众,抹煞爱国运动的事实。此后,不仅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响应,全国各地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成立救国会,声势浩大的救国运动共同体的形成,极大冲击了国民党当局的统治,也为促成国共团结合作提供了有利契机。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的《团结御辱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也是抗战期间很有影响力的一篇历史文献,该文全面阐述了救国会的立场,明确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救国会的主张,并发表公开信进行回应,代表中国共产党向邹韬奋等救国会全体会员表示敬意,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走向新阶段。同年9月18日,毛泽东同志又亲笔写信给邹韬奋等爱国人士表彰其英勇行动,并委托潘汉年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与邹韬奋和救国会正式建立直接联系。此后,邹韬奋总是尽其所能寻找能够接触到的党组织指导实践,自觉以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推动工作,将整个革命的利益视为人生准则,毫无条件地服从于抗日救国全局需要。总之,在这个过程中,邹韬奋已经严格按照一位革命者的标准进行自我要求,全心全意为党工作,为冲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化围剿、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书写了精彩华章。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斗,党领导人民,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合作下,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邹韬奋生前的公开身份是党外民主人士,逝世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但事实上,他早就在思想上入了党。邹韬奋女儿邹嘉骊明确说过:“父亲信仰马克思主义,主要来自他流亡海外期间,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认真阅读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从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真正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早在1938年,邹韬奋就郑重地向周恩来同志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同志给出的答复是:“你现在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在国民党地区和国民党作政治斗争,和你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样,这是党需要你这样做。”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组织文化抗战、传播大众文化,这是我们党给邹韬奋的指令。可以说,邹韬奋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行中共党员之实,为在国统区积极推广大众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周恩来同志就曾经充分肯定邹韬奋的革命贡献:“我们党的抗日救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要是通过韬奋主编的刊物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知识分子中去的。”对于邹韬奋文化抗战的巨大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则如此评价邹韬奋:“我们干革命有两支队伍,武的是八路军,文的是邹韬奋在上海办刊物、开书店。”我们完全可以说,邹韬奋的新闻出版实践、邹韬奋的文化抗战,极大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高扬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联系方式
公众号二维码

微博二维码